今天小編為大家?guī)砹艘黄P(guān)于生物進化論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萬物是如何來的,特別是生命是如何出現(xiàn),并且形成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那般多姿多彩?這既是一個哲學(xué)課題,也幾乎是所有文明從誕生起就不斷努力探索的課題。
《圣經(jīng)》中有創(chuàng)世紀,認為是神創(chuàng)造了天地萬物;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里有盤古開天辟地,又以自己的肉身化為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草木萬物的故事。
對于人類的起源,《圣經(jīng)》說是上帝耶和華仿造自己創(chuàng)造了男人,又用男人的肋骨創(chuàng)造了女人;中國的神話傳說則說是女媧娘娘用黃土、黃河水攪拌成泥巴,捏出了第一批人類。

不同的文明體系,以不同的猜想和神話解釋著生命的起源,這些不同的解釋又衍生出了流派眾多、豐富多彩、個性鮮明哲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甚至是自然科學(xué)。
人類探求生命奧秘的腳步從未停歇,但均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直到19世紀50年代,英國學(xué)者達爾文出版發(fā)行了自己的著作《物種起源》,系統(tǒng)闡述了生物進化論思想。生物進化論的誕生,幾乎具有顛覆性的意義,徹底推翻了此前人們所做的種種設(shè)想,改寫了生物學(xué)、生理學(xué)、生物考古學(xué)等學(xué)術(shù)框架。盡管今天有一些學(xué)者對生物進化論提出了與之相左的某些論點或者證據(jù),但由生物進化論所統(tǒng)攝的生命科學(xué)體系卻依然是堅固而龐大的。
但如果仔細研究中國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思想,就會發(fā)現(xiàn)類似或者非常接近達爾文生物進化論思想的智慧火花,早已經(jīng)在老子、列子、莊子、墨子等思想家的言論中璀璨閃耀了。
在《道德經(jīng)》第四十章,老子就說:“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今天的人們看到這句話要么會感覺到玄虛,要么會感覺到平淡。感覺玄虛是因為老子口中的“道”“有”“無”等均是一些高度抽象的概念,似乎很難讓人真正領(lǐng)悟其中的奧秘。感覺到平淡則因為今天的人們已經(jīng)普遍接受和理解了生物進化論,早已熟悉所有生命從無到有、從無機到有機、從簡單到復(fù)雜、從低級到高級的生成、演化規(guī)則。
但在兩千多年前,老子能夠說出這樣的言語卻是極為難能可貴的。因為從這句話里就可以看出,老子早已經(jīng)摒棄了“神造說”“天生說”,否定了具有人格的超自然力量或者具有自主意識的“天”的存在,展露出了萬物均是從無到有而出現(xiàn)的唯物主義認識。因為不論是“神造說”還是“天生說”,都有一個基本的假設(shè)就是在萬物出現(xiàn)之前,就已經(jīng)有某個具有“框范”意義的存在出現(xiàn)了。從邏輯的角度說,那么這個早于萬物的“框范”又是從何而來的?
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認為,所有生物之所以會進化,其根本動力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老子的這種“有生于無”,否定超自然力量的思想就完全契合。在列子這里,這種推崇自然力而否定對“天”“神”等先天的、絕對存在的、超自然的主宰力量的傾向就更為明顯了。
列子認為:萬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所謂的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其關(guān)鍵就是一個“自”字。“神造說”強調(diào)的是外來的力量,也就是“他”;而列子的“自生說”,則更強調(diào)萬物的本來屬性與自我驅(qū)動。這種“他”與“自”的關(guān)系就相當于哲學(xué)中的外因與內(nèi)因。外因是條件,內(nèi)因是根本,這是基本的哲學(xué)論斷。
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認為,生物生存的外界環(huán)境在不斷變遷,生物之間存在生存競爭,這些都是誘發(fā)生物基因變異的外部條件。而生物進化的內(nèi)因就是,生物具有因為環(huán)境變化而基因變異,并將這種變異積累起來的屬性。生物倘若沒有基因變異的屬性,那么所有的物種就不可能延續(xù)和進化,這是進化并且形成繁復(fù)眾多、數(shù)量龐大的生物群體的基礎(chǔ)。而基因變異的結(jié)果倘若偏離了環(huán)境變化和競爭需要,則這種變異會被淘汰,這個物種也就滅絕了。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列子對“自”的強調(diào)是不是就非常具有進化論的科學(xué)思維了。
佛教在這個方面很聰明,饒過了起源問題。對于世界的出現(xiàn),佛教解釋為“萬法由心,三界唯識”;對于生物的種類,佛教劃分為六道;對生命的生死以及生物的延續(xù),佛教解釋為業(yè)力驅(qū)使。按照佛教的思想,既然生命乃至萬物都是由“心”或者“識”來化現(xiàn)的,那么最初的“心識”又是從何而來的?佛教對此的解釋是,世界是無始無終的。既然沒有“始”,當然就不用去解釋起源問題了。
如果說老子的“有生于無”的思想過于粗略,類似但并未真正接近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思想,那么到了道家的另一個思想莊周這里,生物進化論的味道就愈加濃郁了。《莊子·寓言篇》里有一句話非常精煉:“萬物皆種也,以其不同形而相禪。始卒若環(huán),莫得其倫。”莊子認為,所有的生物在最早的時候都是一樣的,也就是所有生物都是由一顆種子萌發(fā)出來的。用今天的研究成果來看莊子這句話,就相當于所有生物都是由無機物在一個偶然機會生成大分子有機物,然后由低級到高級,有大分子進而形成具有生命特征的細胞、組織、器官、系統(tǒng),以至于豐富多彩的生物世界。所有的生物形態(tài)不同,但其起源的“種”是一致的。
《莊子·秋水篇》里又說:“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如貍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意思是說,雖然所有的生物形態(tài)不同、能力各異,但它們的不同又使他們能夠符合環(huán)境條件和生存需要,這種思想是不是非常類似生物進化論“適者生存”法則?生物進化論的觀點里,并不是最強者才能生存,而是最適合者才能生存。莊子所說的馬善于奔跑,貓頭鷹善于夜視,這都是為了生存需要而“自生”出來的技能。
莊子可以說是在整個先秦時期對于萬物由來和生物進化思考、論述最多也最為深刻的思想家了,他活躍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如果我們將莊子的這些思想認定為生物進化論思想的話,那么這些具有“穿越”意味的言語就比英國的達爾文發(fā)表《物種起源》早了兩千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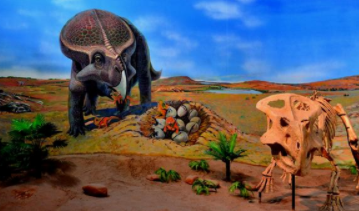
遺憾的是,老子、莊子、列子等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們雖然萌芽了生物進化的思想,但受思想認識、科研條件的限制,并未從形態(tài)學(xué)、分類學(xué)、解剖學(xué)的角度進一步深入研究、扎實論證,使之成為完備、系統(tǒng)、嚴密的學(xué)術(shù)系統(tǒng)。與以上學(xué)者大體在同一時代的墨子是非常具有現(xiàn)代科學(xué)思維特點和研究方法的另一個思想家,他也曾經(jīng)探索過物種起源、生物進化的問題,例如《墨經(jīng)》就有“龜化為鶉”的說法,惠施、公孫龍這兩個名家的哲學(xué)論述里也有“卵有毛”、“犬可以為羊”、“丁子有尾”等提法,但可惜都是片段化的,并沒有深入探究烏龜如何變?yōu)轾g鶉(爬行綱進化為鳥綱)、雞蛋為什么潛藏羽毛的屬性、狗憑什么能成為羊,等等問題,以至于生物進化論的智慧火花雖然已經(jīng)在先秦時期閃現(xiàn)了,但卻未因此而燃起科學(xué)進步的熊熊大火。這不能不說是先秦諸子留給歷史的重大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