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說起崖山之戰(zhàn)的話,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崖山之所以名垂千古,主要在于眾多軍民寧愿投海也不愿投降元軍,一直被后人看作是愛國主義的表現(xiàn)。

那么,歷史上真有如此多的人殉國嗎?
據(jù)史料記載,崖山之戰(zhàn)后一天,即祥興二年(1279年)二月七日早晨,海上浮尸十萬。陸秀夫的尸體被百姓們找到后安葬了;小皇帝趙昺的尸體則被元軍尋得,只見一眉清目秀的小兒身穿龍袍,頭戴皇冠,身上還掛著一個玉璽……
之后,元兵將玉璽交給張弘范,張弘范確認(rèn)這小兒是趙昺,派人尋回,然而趙昺的尸體已經(jīng)下落不明。據(jù)說被百姓埋葬在了廣東深圳赤灣村里,至今仍存。崖山海戰(zhàn)后,宋室覆亡。元將張弘范命人在崖山巖壁上雕刻了“鎮(zhèn)國大將軍張弘范滅宋于此”十二個大字。
陸秀夫的縱身一跳,不僅跳出了一段“神話”,還將自己載入了史冊。
也許,這段場面過于慘烈,連元代的歷史學(xué)家都沒有詳細(xì)記載。只是,在《宋史》的文字之中,簡單地描述了當(dāng)時跳海的人數(shù)有十萬之多。文字記載雖然不夠詳細(xì),但已經(jīng)為歷史提供了足夠的考據(jù)。
然而,單憑這一點,就能確定當(dāng)時的場景,真如文字描述的那般數(shù)字龐大嗎?
其實,在陸秀夫跳海之前,先是逼著自己的妻子跳了海,從自家做起,舉家殉國,這一點連元朝的統(tǒng)治者都佩服不已。和陸秀夫一樣,被人記住的還有劉鼎孫,但是,這位先生跳了兩次,才最終結(jié)束了自己的性命。
想來,陸秀夫背著小皇帝這么一跳,主要是為了做一個“表率”,用自己的行動告訴老百姓:與其被元軍殺了,還不如自行了斷,這樣更痛快一些。而這種舉動放在現(xiàn)在來看,可以用“殘忍”二字來形容了。

那么,這種大規(guī)模的“滅口”,僅僅是一種“忠君”或者“忠國”的表現(xiàn)嗎?
其實,任何一場戰(zhàn)爭都是沖突發(fā)展到極致后的一種結(jié)果,而正是戰(zhàn)爭才解決了這種沖突。要知道,從古到今,用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平衡應(yīng)該是最為公道的一種做法,而不是通過一場戰(zhàn)爭來創(chuàng)造“神話”,如果這樣,那是不是場面越慘越好呢?
然而,可以冷靜下來思考一下,亡國之際,宋朝軍民長途跋涉了那么久,還會有多少人跟著呢?這個不難計算,首先,后宮人員本來就很少,再加上大臣,即使全家一起也湊不齊十萬數(shù)字。所以,這十萬數(shù)字的結(jié)論,極有可能是由于心理上的恐懼而產(chǎn)生的。
當(dāng)時,由陸秀夫、劉鼎孫二人帶頭,已經(jīng)給了跟隨者心理上一個暗示,讓他們在心中認(rèn)定:自殺就是自己的唯一出路。雖然,大家對于生是如此的渴望,但是,在恐懼中也就只剩下了這么一條路了。
另外,也不排除是陸秀夫、劉鼎孫二人逼著老百姓跳海的可能。
本來,在他們的眼中天下都是皇帝的,老百姓也不過是皇帝的私人“東西”罷了。既然皇帝都不能活了,那么,他們?yōu)槭裁催€要留在這個世間?當(dāng)然都得隨著皇帝一起“走”了。如果這個推論成立,只能說明跳海事件是殉葬制度的一個延伸罷了。
這么看來,這個著名的歷史事件,有可能是一場人為制造的陪葬悲劇。而用十萬人陪葬,是不是有點太“暴力”了?與此同時,還被后世冠以“殉國”的大帽子,讓大家覺得這一切都是“自覺”發(fā)生的。并且,老百姓一直都是是盲從的。
因為,他們認(rèn)為官方說的話,即使不正確也得照做,根本就沒有想過拒絕,因為,在皇權(quán)至上的年代,似乎也沒有其它選擇。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這么聽話呢?
當(dāng)時,有個叫張世杰的人很有主見,覺得可以去別的地方再建一個政府。但可惜,張世杰的想法被其他人阻止了,并被迫離開了崖山。
然而,除了崖山,就沒有其它退路了嗎?
可能大家已經(jīng)忘了,還有一處地方,那就是:海南,它再小,也能容下這么多人。但為何大家寧愿一死,也不愿去海南呢?是和面子有關(guān)嗎?
其實,在宋代時期海南是收容流放人員的。曾經(jīng),年已六十二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的海南島儋州。可以說,在當(dāng)時流放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了。所以,蘇軾把儋州當(dāng)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xiāng),“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
后來流放海南的還有許多主戰(zhàn)派的大臣。
所以,一想到自己要逃往海南這個流放之地,這些人是不是覺得有種打臉的感覺?明明有生路,卻為了顏面,讓大家陪著皇帝一起跳海,這種做法似乎有點過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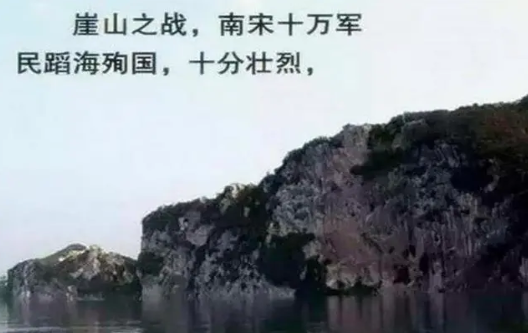
這里,我們暫且不管這十萬數(shù)字是否屬實,也暫且不管為何有那么多人一起跳海。其實,在很多人的眼中,崖山之戰(zhàn)體現(xiàn)的愛國情懷也許就是皇權(quán)思想在作怪。在最后一刻,雖然,都要維護皇權(quán)的“尊嚴(yán)”,但這么一跳真的可以改變歷史嗎?
說句不好聽的話,縱身一跳的行為只不過是空耗生命罷了。
如果人口的消耗可以改變歷史,那未嘗不可嘗試一下。但是,以這種“自殘”的方式宣告自己“不服輸”,只會讓對方高興。因為,在歷史上,最難統(tǒng)治的就是“人心”。試想一下,一個國家,最有“節(jié)氣”的那些人都沒了,他們還擔(dān)心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