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的中書制度,下面小編為大家?guī)?lái)詳細(xì)的介紹。讓我們一起來(lái)看看吧!
曹魏建立后,沿襲漢制設(shè)立了中書制度,基于中書制度而產(chǎn)生的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在曹魏時(shí)期權(quán)力很大,許多人視為宰相。曹魏最有名的兩位中書官員-中書令孫資和中書監(jiān)劉放,甚至在魏明帝病篤時(shí),利用魏明帝無(wú)法言語(yǔ)的機(jī)會(huì),強(qiáng)迫魏明帝改詔,啟用曹爽和司馬懿為顧命大臣,換掉了魏明帝之前擬定的由宗室成員輔政的顧命大臣名單。孫資和劉放以中書的身份,強(qiáng)迫魏明帝改詔之舉,為日后司馬懿篡權(quán)提供了契機(jī),改寫了曹魏的命運(yùn)。
在很多人看來(lái),曹魏的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就是位高權(quán)重的宰相,連敢逼皇帝修改遺詔,可見(jiàn)中書權(quán)力之大。真相真的如此嗎,中書在曹魏到底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
曹魏中書制度概況
中書最早誕生于漢武帝時(shí)期,其職責(zé)和尚書差不多,即傳達(dá)文書、奏章。曹魏建立后,中書的職級(jí)很低,職責(zé)就是替皇帝起草政令、詔令和各種文書。中書在曹魏成為獨(dú)立的機(jī)構(gòu),以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為長(zhǎng)官。除此之外,還有若干中書侍郎作為辦事員。

中書作為皇帝近侍,可以利用皇帝的寵信來(lái)達(dá)到獨(dú)斷專行的目的,這一點(diǎn)非常受人詬病。魏文帝和魏明帝時(shí)期,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權(quán)力極大,“號(hào)為專任”,一旦擔(dān)任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的品質(zhì)不行,就可以利用中書的權(quán)力為所欲為。重臣蔣濟(jì)就曾上疏魏明帝,批評(píng)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權(quán)力過(guò)重,有危害社稷之虞。
大臣太重者國(guó)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nèi)扇動(dòng)。陛下卓然自覽萬(wàn)機(jī),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quán)在下,則眾心慢上,勢(shì)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無(wú)忘于左右。左右忠正遠(yuǎn)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shí)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jiàn)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時(shí)而向之。-《三國(guó)志·魏志·蔣濟(jì)傳》
蔣濟(jì)的這份上疏,對(duì)中書專權(quán)的行為進(jìn)行了嚴(yán)厲批評(píng),認(rèn)為這會(huì)帶來(lái)嚴(yán)重的政治后果。所謂“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說(shuō)的就是中書作為皇帝的近侍,可以利用皇帝精力不濟(jì)之際,對(duì)朝政施加影響,從而達(dá)到控制朝堂的目的。
從蔣濟(jì)的上疏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中書不在朝臣之列,僅僅是皇帝身邊的侍從而已。中書的權(quán)力來(lái)源于皇帝的授予,而非制度使然。盡管中書有干預(yù)朝政的權(quán)力,但這種權(quán)力并不符合制度規(guī)定,僅僅是皇帝憑自己的喜好授權(quán)而已。由此可見(jiàn),曹魏的中書權(quán)力的確很大,但權(quán)力來(lái)源于皇帝而非制度。
那么為什么曹魏的中書權(quán)力這么大?這和當(dāng)時(shí)的三國(guó)局勢(shì)有關(guān)。三國(guó)亂世,戰(zhàn)事頻繁、政局動(dòng)蕩。為了建立一個(gè)穩(wěn)固的統(tǒng)治政權(quán),就必須讓皇帝本人大權(quán)獨(dú)攬。所以魏文帝和魏明帝時(shí),他們都總攬朝政,政由己出。這是導(dǎo)致曹魏中書權(quán)力膨脹的主要因素。為了加快統(tǒng)一全國(guó)的步伐,魏文帝和魏明帝大權(quán)獨(dú)攬,往往繞過(guò)三公這些宰相,直接通過(guò)中書來(lái)處理政務(wù),和一線辦事官員直接溝通對(duì)話。另一方面,隨著曹魏政權(quán)相對(duì)穩(wěn)定以后,魏文帝和魏明帝就開(kāi)始貪圖享樂(lè),對(duì)政務(wù)沒(méi)有以前用心了,再加上能力有限,如果政事不決時(shí),不去找外朝的朝臣商量,而是和身邊的中書商量,讓“掌王言”的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替他們拿主意。

在政事方面,魏明帝動(dòng)輒問(wèn)計(jì)于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的例子,比比皆是。魏明帝大權(quán)獨(dú)攬,卻很少召開(kāi)公卿會(huì)議,所以遇到問(wèn)題了,首先想到的是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
是時(shí),孫權(quán)、諸葛亮號(hào)稱劇賊,無(wú)歲不有軍征。而帝總攝群下,內(nèi)圖御寇之計(jì),外規(guī)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dòng)大眾,舉大事,宜與群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huì)議,資奏當(dāng)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己之德也。-《三國(guó)志·魏志·孫資傳》
皇帝政由己出,但是能力有限時(shí),不得不依靠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來(lái)協(xié)助自己理政,這是曹魏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權(quán)力膨脹的根本原因。
中書如何影響朝政
曹魏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權(quán)力非常大,必然會(huì)利用自己的權(quán)力,對(duì)朝政施加影響。中書對(duì)曹魏朝政的影響,當(dāng)然是多方面的,不過(guò)最主要體現(xiàn)在朝廷的人事安排上。該由什么樣的人出任什么樣的官職,甚至安排什么樣的人輔政,中書都能發(fā)表自己的意見(jiàn),而且他們的意見(jiàn)對(duì)皇帝影響很大。在人事安排方面,中書擁有很重的建議權(quán),借此影響朝政,甚至影響了曹魏的國(guó)祚。
侍中辛毗為人正直,當(dāng)時(shí)中書令孫資和中書監(jiān)劉放深受魏明帝寵信,是魏明帝身邊的紅人,許多官員都跑去巴結(jié)孫資和劉放,但是辛毗卻從來(lái)不和孫資、劉放往來(lái)。再加上辛毗秉公辦事,平日也有不少得罪孫資、劉放的地方,所以孫資、劉放頗為嫉恨辛毗。

有司上表魏明帝,說(shuō)尚書仆射王思才能力不足,明顯不如辛毗,建議讓辛毗代替王思。魏明帝聞奏后,于是咨詢孫資、劉放的意見(jiàn),孫資、劉放不樂(lè)意辛毗出任尚書仆射這么重要的官職,于是非常委婉得地詆毀辛毗,不建議由辛毗出任尚書仆射。魏明帝聽(tīng)從了孫資、劉放的意見(jiàn),就沒(méi)有讓辛毗轉(zhuǎn)任尚書仆射,而是“出為衛(wèi)尉”。
時(shí)中書監(jiān)劉放、令孫資見(jiàn)信于主,制斷時(shí)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lái)……冗從仆射畢軌表言:"尚書仆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jì)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duì)曰:"陛下用思者,誠(chéng)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毗實(shí)亮直,然性剛而專,圣慮所當(dāng)深察也。"遂不用。出為衛(wèi)尉。-《三國(guó)志·魏志·孫資傳》
魏明帝欲用辛毗為尚書仆射,為什么會(huì)咨詢孫資、劉放的意見(jiàn)呢?因?yàn)榘凑詹芪旱闹贫龋实廴蚊橙顺鋈文彻俾殨r(shí),需要由中書令或者中書監(jiān)起草相應(yīng)的詔令。所以魏明帝詢問(wèn)孫資、劉放的意見(jiàn),也是很自然的。孫資、劉放因?yàn)楹托僚邢酉叮驼Z(yǔ)帶玄機(jī)地暗示辛毗不適合轉(zhuǎn)任尚書仆射。問(wèn)題是,魏明帝為什么會(huì)聽(tīng)他們的?這當(dāng)然和魏明帝對(duì)他們的寵信是有關(guān)系的。孫資、劉放暗示辛毗不時(shí)任,魏明帝就放棄了對(duì)辛毗的任命。這說(shuō)明魏明帝是非常信任他們的,他們的意見(jiàn),對(duì)魏明帝有重要影響。
在任命尚書仆射這樣重要的官職上,魏明帝不去咨詢外朝公卿大臣的意見(jiàn),而是隨意問(wèn)一下身邊的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就決定要不要任命。可見(jiàn)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在人事安排上,能對(duì)皇帝施加足夠的影響。皇帝對(duì)中書的高度信任,這也是中書令和中書監(jiān)權(quán)力膨脹的根本所在。
魏明帝臨終前,擬定了這樣一份輔政大臣名單:燕王曹宇為大將軍,與領(lǐng)軍將軍夏侯獻(xiàn)、武衛(wèi)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這份輔政大臣名單,體現(xiàn)了魏明帝的兩個(gè)意圖。
一是魏明帝倚重宗室的目的的非常明顯。這個(gè)名單以燕王曹宇為首,主要包括了曹魏的宗室和皇親國(guó)戚。曹宇是曹操的親兒子,妥妥的宗室;曹肇是大司馬曹休的兒子、曹爽是大將軍曹真的兒子,這兩人屬于皇親國(guó)戚。夏侯獻(xiàn)雖然身份不明確,但出身夏侯氏,應(yīng)該是皇親國(guó)戚了。秦朗是曹操的養(yǎng)子,和魏明帝關(guān)系不錯(cuò),自然也是皇親國(guó)戚了。可以看得出,魏明帝是很依賴曹氏宗親的,就像魏明帝自己所說(shuō)的那樣,“圖萬(wàn)年后計(jì),莫過(guò)使親人廣據(jù)職勢(shì),兵任又重。”
二是魏明帝排斥司馬懿動(dòng)作非常明顯。司馬懿作為戰(zhàn)功卓著的元老勛臣,理應(yīng)在輔政大臣之列,但魏明帝卻有意把他排除在外。這實(shí)際上顯示了魏明帝對(duì)司馬懿的懷疑和不安。當(dāng)初因?yàn)橹T葛亮北伐,給曹魏帶來(lái)了很大的軍事壓力,而曹真又病重?zé)o法任事,魏明帝不得不啟用司馬懿坐鎮(zhèn)關(guān)中抵御諸葛亮,司馬懿由此掌握了兵權(quán)。隨著諸葛亮的病死,蜀漢暫時(shí)了停止了北伐,曹魏所面臨的軍事壓力驟然減輕,那么削弱司馬懿的權(quán)勢(shì),也當(dāng)然在魏明帝的計(jì)劃中。這很自然地體現(xiàn)在,司馬懿并未出現(xiàn)在輔政大臣名單中。

魏明帝的這個(gè)輔政大臣名單,就當(dāng)時(shí)的情勢(shì)而言,是非常合理的安排。如果能施行,那么對(duì)曹魏國(guó)祚當(dāng)然是很有利的。但這個(gè)輔政大臣名單,因?yàn)樵獾街袝顚O資和中書監(jiān)劉放的破壞,而無(wú)法施行。他們利用中書親近皇帝的權(quán)力,借魏明帝病篤無(wú)法言語(yǔ)之際,強(qiáng)迫魏明帝修改輔政大臣名單。孫資和劉放乘著魏明帝氣息微弱,握住魏明帝的手強(qiáng)行修改了輔政大臣名單,遂定曹爽和司馬懿共同輔政。嚴(yán)格來(lái)說(shuō),孫資和劉放這是典型的矯詔,那么為什么他們敢矯詔呢?
這當(dāng)然是因?yàn)橹袝鴻?quán)力巨大,孫資和劉放仗著魏明帝的信任,平日囂張跋扈慣了,再加上魏明帝此時(shí)也氣息奄奄,沒(méi)有敢阻攔他們。孫資和劉放權(quán)力之大,居然可以決定曹魏帝國(guó)的輔政大臣人選,而且連皇帝也無(wú)可奈何。他們把司馬懿引入輔政大臣名單,為日后司馬氏篡魏埋下了禍根。
孫資和劉放強(qiáng)迫魏明帝改詔一事,正應(yīng)了蔣濟(jì)所說(shuō)的“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而且也暗合了他們“見(jiàn)信于主,制斷時(shí)政”。由此可見(jiàn),中書能利用皇帝的信任從而對(duì)朝政施加影響。
曹魏中書為什么不是宰相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曹魏的中書,的確權(quán)力非常大。所以不少人把中書視為曹魏的宰相,這當(dāng)然是一葉障目不見(jiàn)泰山,并不準(zhǔn)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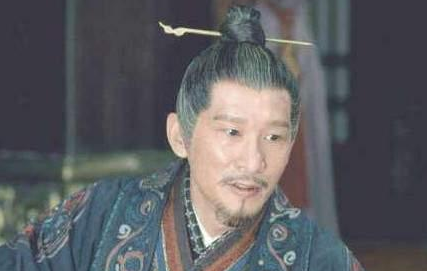
目前主流觀點(diǎn)認(rèn)為,宰相應(yīng)該同時(shí)具有議政權(quán)和統(tǒng)領(lǐng)、監(jiān)督百官的權(quán)力。實(shí)際上史學(xué)界絕大部分人也都認(rèn)可這個(gè)觀點(diǎn),這明確定義了宰相的職權(quán)。
那么按照以上所定義的宰相標(biāo)準(zhǔn),曹魏的宰相是什么官職呢?其實(shí)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宰相是不同的,前期和中期三公是宰相,后期尚書是宰相。就歷史發(fā)展來(lái)看,總體趨勢(shì)是,曹魏的宰相職權(quán)逐步從三公過(guò)渡到尚書,和中書沒(méi)有太大關(guān)系。
曹魏帝國(guó)建立后,延續(xù)了東漢的三公制度,三公仍然發(fā)揮著宰相職能,不僅有議政權(quán),還有統(tǒng)領(lǐng)、監(jiān)督百官的權(quán)力。但是從魏文帝到魏明帝,尚書一步步侵奪三公的宰相職權(quán),使得三公逐漸淪為虛職。三公逐漸被尚書架空,尚書也逐步朝著宰相方向發(fā)展著。到了魏帝曹芳時(shí)期,尚書基本取代三公,成為事實(shí)上的宰相。
曹魏初期全國(guó)各地奏章一般都交給三公府處理,但是后來(lái)逐步轉(zhuǎn)移到尚書臺(tái)。尚書對(duì)奏章給出初步意見(jiàn)后,再交給皇帝定奪。事實(shí)上,到了曹魏后期,已經(jīng)見(jiàn)不到三公處理奏章的事例了,而是由尚書在處理奏章。
曹魏時(shí)期由于政治形勢(shì)的發(fā)展,尚書臺(tái)不斷侵奪三公府的宰相權(quán)力,特別是曹魏后期,曹爽和司馬懿爭(zhēng)權(quán)時(shí),因?yàn)槲簳x嬗代所引發(fā)的政治斗爭(zhēng)的需要,尚書逐漸取代三公,成為曹魏事實(shí)上的宰相。
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lái),九列執(zhí)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于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tǒng),若丞相之為。-《晉書·劉頌傳》
以上這段史料幾乎可以看作古代宰相定義的標(biāo)尺,向我們說(shuō)明了由魏入晉以后,尚書則不僅完全掌握議政權(quán),同時(shí)還是文武百官之首,并能監(jiān)督百官的執(zhí)行情況,成為公認(rèn)的宰相。

讓人疑惑的是,尚書完全符合宰相的定義標(biāo)準(zhǔn),也確實(shí)就是宰相。那為什么中書還擁有那么大的權(quán)力,甚至超過(guò)了尚書,卻不能被稱作宰相呢?
其實(shí)前文就有提到這一點(diǎn),那就是中書的權(quán)力,來(lái)源于皇帝寵信,而非制度賦予。在制度上,曹魏中書的權(quán)力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中書受到皇帝的寵信,就能獲得極大的權(quán)力。孫資和劉放敢強(qiáng)迫病篤中的魏明帝改詔,硬是把推翻了魏明帝原先的托孤安排,就是因?yàn)槿绱恕V袝軟Q定輔政大臣人選,確實(shí)說(shuō)明了中書具有左右政局的能力。中書甚至“號(hào)為專任”,這也是很多人把中書視為“宰相”的重要原因。
但我們也要看到,中書權(quán)力之重,并不是制度規(guī)定的,而是皇帝寵信的結(jié)果。中書的本職工作就是替皇帝起草詔令,至于詔令的內(nèi)容,當(dāng)然是皇帝所決定的。在制度上,中書無(wú)權(quán)干預(yù)皇帝起草什么內(nèi)容的詔令,自然也就談不上議政權(quán)了。因?yàn)槲何牡酆臀好鞯劢?jīng)常咨詢中書,才使得中書可以影響朝廷決策。而且中書作為皇帝近侍,自然無(wú)法統(tǒng)領(lǐng)外朝的文武百官,更談不上監(jiān)督百官的執(zhí)行情況。中書的“宰相”名號(hào),當(dāng)然無(wú)從談起。
魏晉以來(lái),中書監(jiān)令掌贊詔命,記會(huì)時(shí)事,典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因其位,謂之鳳凰池焉。-《通典》
這段史料除了介紹中書的基本職責(zé)之外,還用了“鳳凰池”這樣的溢美之詞,既向我們展示了中書的權(quán)勢(shì)之盛,又說(shuō)破了中書權(quán)力之盛的原因。那就是“地在樞近,多承寵任”,因?yàn)槭怯H近皇帝而被授予重權(quán)。
高平陵之變后,司馬家族掌權(quán)。此時(shí)皇權(quán)衰落,借助皇帝寵信而興盛的中書,其權(quán)勢(shì)明顯下降。司馬家族掌控曹魏時(shí),紛紛安排自己的親信,進(jìn)入曹魏的顯要部門,其中最受重視的就是尚書臺(tái)。司馬家族的親信荀顗、何曾、裴秀、陳騫、傅嘏等人都入主尚書臺(tái)。至于中書,司馬家族則沒(méi)有安插任何親信。如果中書真有那么重要,司馬家族顯然不會(huì)忽視。尚書和中書,孰重孰輕。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