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黃金量的變化對社會(huì)也會(huì)產(chǎn)生影響,那么在東漢時(shí)期黃金量的變化帶來了哪些影響呢?下面小編給大家?guī)砹讼嚓P(guān)內(nèi)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討論貨幣本位之前,首先要討論兩漢時(shí)期的黃金是否為貨幣。從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學(xué)上來看,貨幣需具備五大職能,包括價(jià)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功能、儲(chǔ)藏手段以及世界貨幣,黃金在先秦兩漢時(shí)期主要用作進(jìn)貢、賞賜、懲罰、行賄以及流通和作為價(jià)值尺度,可見其具有貨幣基本的支付、儲(chǔ)藏、價(jià)值尺度、支付功能,而世界貨幣功能就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來看,各個(gè)諸侯國都是一個(gè)獨(dú)立的國家。
所以其中的交往與貿(mào)易往來可看作是國際貿(mào)易,漢代更是如此,其與西域、東亞、南亞甚至歐洲諸國都存在一定的商貿(mào)往來,因此當(dāng)時(shí)的黃金同樣具備世界貨幣功能。馬克思說:“當(dāng)作價(jià)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過代表作為流通手段來執(zhí)行職能的商品,是貨幣。因此金(或銀)是貨幣”,因此先秦兩漢時(shí)期的黃金確實(shí)是貨幣。
一、對古陸路絲綢之路貿(mào)易的影響
1.絲綢之路的誕生
“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由李希霍芬首先提出的,此概念后多用來形容15世紀(jì)之前從長安經(jīng)中亞通往南亞、西亞和歐洲的東西方通道。絲綢早在秦代就已經(jīng)開始用于交換貿(mào)易,秦人烏氏倮就是一個(gè)代表。

他是一位生活在秦代固原地區(qū)的戎族畜牧業(yè)生產(chǎn)者,“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xiàn)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他把牛羊變賣給中原農(nóng)耕區(qū)的農(nóng)民,換成絲織品和寶物然后獻(xiàn)給戎王,戎王奉還給他數(shù)十倍的牛馬。而戎王用這些珍寶和絲織品“向盤踞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和塞人交換他們從中亞、西亞、羅馬人手中交換來的黃金”。古羅馬貴金屬礦藏稀缺,黃金資源十分緊俏,“對于金銀器的保護(hù)甚至寫入了十二銅表法內(nèi)——喪葬不得使用金銀陪葬”。可知當(dāng)時(shí)古羅馬對黃金的需求日益擴(kuò)大,他們只能通過戰(zhàn)爭對外掠奪,其與迦太基進(jìn)行了長達(dá)百年的布匿戰(zhàn)爭,第二次布匿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羅馬軍隊(duì)從撒馬城“掠奪了3000公斤黃金”。
到了西漢時(shí)期,武帝曾派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通往西域之路由此暢通,“在張騫的強(qiáng)烈建議下,漢武帝還招募了一大批身份低微的商人,鼓勵(lì)他們利用政府的支持貿(mào)易政策與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jīng)商”,從此之后這條路上的貿(mào)易也逐漸興盛。當(dāng)時(shí)漢王朝和古羅馬都處于擴(kuò)張的過程中,而雙方的交集點(diǎn)就在西域地區(qū),兩國之間的貿(mào)易活動(dòng)從張騫鑿空西域之后變得更加頻繁。
2.羅馬的策略
羅馬將戰(zhàn)爭掠奪來的黃金大都用在對外貿(mào)易上,其中漢朝也是較大的受益者,購買漢朝的絲綢消耗了羅馬的大量黃金。“羅馬在共和時(shí)代(西漢及以前)雖然不以黃金鑄錢,但對外支付,是用黃金……在帝國時(shí)代(相當(dāng)于東漢)更是使用金幣。所以當(dāng)時(shí)的世界貨幣,即中國同西方的交易媒介,自然是黃金……羅馬史家普里尼說……七千五百萬以上約合黃金五千多公斤,應(yīng)當(dāng)是流到中國和阿拉伯”。
除了絲綢與黃金的交換,還有一些帶有典型西方紋樣和工藝的金器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往中原內(nèi)陸,并被內(nèi)地工匠們廣泛模仿制作、流傳,本文第一章中已分析過外來金器的傳播路線,可以明確西漢時(shí)期的黃金制品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jìn)行傳播。東漢時(shí)期,草原絲綢之路的貿(mào)易依然興盛。位于今阿富汗的“黃金之丘”曾出土過三枚黃金貨幣,一枚帕提亞金幣,一枚羅馬帝國金幣以及一枚印度金幣,其中帕提亞金幣磨損十分嚴(yán)重,應(yīng)當(dāng)是經(jīng)過長時(shí)間的流通才埋入墓葬中,其他兩枚金幣則磨損輕微,沒有流通用的戳印,應(yīng)當(dāng)未經(jīng)過長期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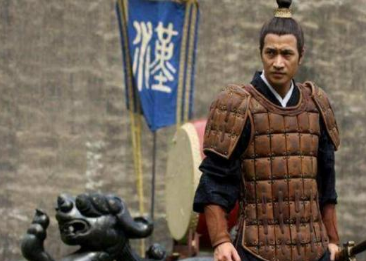
《漢書·西域傳》言大月氏國“民俗錢幣,與安息同”,這與流通時(shí)間較長的帕提亞金幣相契合。有研究認(rèn)為“由于羅馬—西北印度—大月氏貿(mào)易路線的開通,大月氏開始使用羅馬、西北印度金幣”,而這一時(shí)期中國剛好處在東漢初期,與當(dāng)時(shí)西域的大月氏交往頻繁,西域流行使用貴霜錢幣,由于貴霜帝國與羅馬貿(mào)易頻繁從而導(dǎo)致羅馬金幣也流入西域地區(qū),而貴霜所“鑄造的金幣與羅馬金幣的純度以及重量完全相同”。
“黃金之丘”同樣出土過幾件具有中國元素的金器,其年代橫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這時(shí)中國處于兩漢時(shí)期。比如出土于號(hào)墓的驅(qū)龍戰(zhàn)車飾件,從其束發(fā)和深衣寬袍的特點(diǎn)可以確定為漢代士大夫形象。還有關(guān)于龍形象的一件金頭飾,雙龍中間國王的穿著應(yīng)屬中亞服飾,但龍卻具有典型的東方元素。郭物根據(jù)龍形上唇翻卷的形態(tài),認(rèn)為該器型起源于商周時(shí)期的翻唇龍形神獸。
無獨(dú)有偶,在今哈薩克斯坦的伊塞克古墓中同樣出土了帶有中國元素的鳥喙鳥爪紋金飾牌,融合了先秦玉文化的谷紋、楚繡中的鳳紋以及兩漢時(shí)期的卷云紋。這些金器的出土說明兩漢時(shí)期的文化元素曾通過絲綢之路到達(dá)遙遠(yuǎn)的中亞乃至阿富汗地區(qū),這些地區(qū)均處于絲綢之路的要沖,起到連接中亞和西亞的作用。“黃金之丘”出土的兩件金器上還具有典型的中亞元素——綠松石,因此本文推測這兩件器物應(yīng)當(dāng)是受到中國紋樣的影響并用本土的鑲嵌綠松石的技術(shù)在當(dāng)?shù)刂谱魍瓿桑魑锉旧砭褪俏幕Q(mào)易交流的證明。但由于東漢與西域地區(qū)的“三通三絕”,草原絲路貿(mào)易隨著通與絕經(jīng)歷了三次興盛與中斷,雖然后期絲綢之路上的商人依然往來不絕,但中間經(jīng)歷的多次戰(zhàn)亂對經(jīng)濟(jì)和貿(mào)易的發(fā)展還是有一定影響。海上絲綢之路一詞最早由法國漢學(xué)家沙畹提出,早在西漢或秦時(shí)就已經(jīng)形成,秦始皇派徐福東渡日本求長生不老藥,這或許是最早的海上航線。

二、海上貿(mào)易
1.史書記載
關(guān)于西漢時(shí)期的海上貿(mào)易,《漢書·地理志》有詳細(xì)記載當(dāng)時(shí)的航程、所需時(shí)間、可抵達(dá)國家以及貿(mào)易貨品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xiàn)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yīng)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賚黃金雜緒而往”,可見黃金和絲綢也在海上貿(mào)易的貨物之中。東漢時(shí)期的海上貿(mào)易也逐漸繁榮,《后漢書·西域傳》載,大秦“土多金銀……以金銀為錢……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166年大秦安敦國王派遣使節(jié)經(jīng)海上通道,來到中國覲見東漢桓帝,進(jìn)貢犀牛角、象牙等貢品,“并無珍異”,這是中國和歐洲國家擺脫了陸路的中轉(zhuǎn)直接通過海上通道交流的記載。
合浦在當(dāng)時(shí)是東西方海上貿(mào)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從合浦出發(fā)帶到東亞、南亞等國的絲織品和黃金,換回來玻璃、珠飾和一些帶有外國文化因素的金珠,而這些傳入本國的東西又從合浦出發(fā)傳入內(nèi)地,影響了當(dāng)?shù)啬承┻_(dá)官貴人的生活。這一點(diǎn)從合浦地區(qū)的考古發(fā)掘成果中也可看出,比如東漢時(shí)期所流行的多面金珠,其出土地點(diǎn)包括今新疆、湖南、廣州以及江蘇等地,其中又以廣州出土數(shù)量為最多。本文在第一章中論述了這種多面金珠的大致傳播通道,廣州和江蘇的金珠制品或許是從海上絲綢之路由南亞諸國傳播而來,經(jīng)過當(dāng)時(shí)的廣州合浦縣再北上到達(dá)江蘇沿海地區(qū),或者直接到達(dá)廣州,再由廣州傳到江蘇地區(qū)。而湖南地區(qū)則可能從希臘羅馬一帶經(jīng)由西域而傳入中原內(nèi)陸,可見東漢時(shí)期的草原絲綢之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是兩條貿(mào)易活動(dòng)同時(shí)興盛的線路。
2.考古發(fā)掘
但從考古發(fā)掘來看,東漢時(shí)期海上絲綢之路所出土的黃金制品要明顯多于草原絲綢之路,但由于東漢朝廷的黃金儲(chǔ)備量不如西漢時(shí)期大,從而導(dǎo)致東漢政府與東南亞、中亞諸國交換的黃金器物隨之減少。由此可見,西漢時(shí)期草原絲綢之路是西漢王朝與中亞、西亞甚至歐洲進(jìn)行貿(mào)易交往的主要途徑,且由于西漢時(shí)期黃金數(shù)量巨大,這條路上不論西傳還是東進(jìn)的黃金貨幣和黃金器物都十分豐富,而東漢時(shí)期由于朝廷儲(chǔ)存的黃金不多,在草原貿(mào)易中未曾有關(guān)于黃金貨物的大宗貿(mào)易往來,且由于軍事原因?qū)е虏菰z路貿(mào)易經(jīng)歷三通三絕,前后共歷經(jīng)長達(dá)百余年的貿(mào)易停滯期,導(dǎo)致草原絲路貿(mào)易大不如西漢時(shí)期,盡顯衰頹之勢。與此同時(shí),東漢時(shí)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貿(mào)易卻逐漸興盛,與東南亞諸國的交往日益密切,其中多為通過港口傳入內(nèi)地的黃金制品,出口國外的金制品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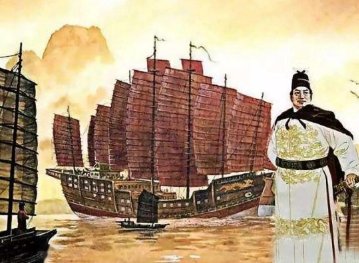
結(jié)語
金本位就是以具有一定重量和含金量的黃金作為主要貨幣的制度,這一體系下要求貨幣必須與黃金掛鉤,貨幣供應(yīng)一定是受到黃金數(shù)量的限制,而黃金作為稀有的貴金屬,在中國古代的產(chǎn)量并不高。根據(jù)夏湘蓉編著的《中國古代礦業(yè)開發(fā)史》中對歷代金礦的整理,可以看出從魏晉到明清,我國的金產(chǎn)地以及金產(chǎn)量并不豐富。基于本章第一節(jié)中所論述的東漢黃金的貨幣功能因莊園經(jīng)濟(jì)居于壟斷地位而逐漸減退,裝飾功能日占上風(fēng)。
魏晉以降,佛教興盛,黃金的裝飾功能達(dá)到了高峰,造像涂金,佛經(jīng)貼金,《魏書·釋老志》記載“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隋唐時(shí)期的金產(chǎn)地大部分都從先秦兩漢繼承而來,多了陜西、甘肅兩省,其產(chǎn)地?cái)?shù)無法跟銅、鐵相比,甚至比不過同為貴金屬的銀,隋唐時(shí)期除了河北、天津、江蘇、貴州和云南五省不產(chǎn)銀之外,其余省份都有多處產(chǎn)銀地。
宋代已經(jīng)有明確的產(chǎn)量記載,以元豐元年為例,銀的年產(chǎn)量為215385兩,而黃金僅為10710兩。遼金元時(shí)期,元代的銀礦和金礦數(shù)量都比宋代有了明顯增多,“天歷元年全國銀產(chǎn)量約為287505兩,大抵相當(dāng)于北宋時(shí)期銀的年產(chǎn)量”,明清時(shí)期采銀業(yè)發(fā)展到頂峰,清代在云南一省的開采的銀廠就有31處之多。相反,清代“金礦不多,產(chǎn)量不大”,直到鴉片戰(zhàn)爭后才屬于開采黃金的興盛時(shí)期。因此基于黃金在我國歷代的產(chǎn)量都不多,不足以制作足量的黃金貨幣以供使用,因此我國古代不具備形成金本位的條件也不可能形成金本位。
